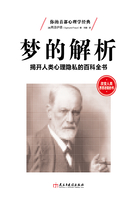
第12章 梦的素材与根源(1)
自分析了伊玛打针的梦之后,我们知道梦是一种愿望的实现;可是紧接着我们便始终都把兴趣集中于此论点的研讨与证明上,以期望能找出梦的一般通性;我们因此也在解析梦的过程中,多少忽略了其他一些特殊的问题。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找到了终点,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另外寻一条道路,以对梦做更深入的研究。也许此后我们将极少提及“愿望的实现”,可是将来我仍然会做一综合结论的。
目前,我们已经知道,遵循着解析的手法,我们能够由梦的“显意”看出更具有意义的梦的“隐意”,可是在“显意”中所显示的哑谜与矛盾一般无法满足我们解释梦的工作,所以,对于每个梦做更加详尽的探究,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以前的学者对梦与醒觉状态的关联,以及梦的素材与根源所发表过的意见,我在这里不想详述,可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出三个常常被提到,但又从未清楚解析过的看法:
(1)梦总是用最近几天印象比较深的事作为内容。
(2)梦选择素材的原则彻底迥异于醒觉状态的原则,而是专门寻找一些次要的易被忽视的小事。
(3)梦彻底受孩提时最初印象所摆布,而且,往往把那段日子的细节、那些在醒觉时根本回忆不起来的小事翻旧帐般地搬出来。
诚然,他们对于这些有关梦的素材的选择所做的每种看法,都是以梦的“显意”为准的。
一、梦中的近期印象和未有关联的印象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梦内容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几乎在每一个梦中均发现它的根源就在做梦的前一天的体验”。其实,不仅我一人这样,大多数的人也都有此感。根据这个事实,我通常在解析梦时,首先问清做梦的前一天内发生了何事,然后尝试着在此找出一些头绪。就大多数个案而言,这确实是一条捷径,以上章我曾经分析过的两个梦(伊玛的打针和长着黄胡子的叔父)来看,确实一问起前天的事,整个疑问就水落石出了,然而,为了更进一步证实它是多么真实,我想从自己的“记梦本”中抄摘几段以飨读者。以下我准备举出一些与梦的内容根源问题有关系的几个梦例:
1.我去拜访一位十分不愿接待我的朋友,……可是,同时却使一个妇人等待着我。
根源:这天晚上有位女亲戚曾经与我谈到她宁愿等到她所需要的汇款到手,一直到……
2.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种植物的学术专论。
根源:早上我在书商那里看到一本关于樱草属植物的学术专论。
3.我遇到一对母女在街上走过,那女儿是一个病人。
根源:在这天晚上,一位接受我治疗的女病人,曾经对我诉苦,说她母亲反对她继续到这儿来接受治疗。
4.在S&R书画店,我订购一份每月定价20佛罗林[5]的期刊。
根源:那天我太太提醒我,每周应该给她的20佛罗林尚未给她。
5.我收到社会民主委员会的信,并且称我为会员。
根源:我同时收到筹划选举的自由委员会的信,以及博爱社主席的来函,而实际上,我的确是后者的一个会员。
6.一个男人,如同伯克林一样,从海里沿峭壁如履平地地走上来。
根源:妖岛上的德雷弗斯以及别的一些由美国的亲戚所说的消息等等。
现在,紧接着我们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梦果真只是由于大的刺激所导致的吗?或者是在最近的一段时期所得的印象都可影响梦的产生?这固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可是我却愿意在这里先对当天所发生的事,对梦所影响的重要程度进行探讨。只要我发觉我的梦的来源是两三天前的印象,我就格外细心去考虑它,从中可以发现这虽是发生在两三天前的事,可我在做梦前一天曾经想到这件事。也就是说,那“印象的重现”曾出现在“发生事情的时刻”与“做梦的时刻”之间,而且,我可以指出很多最近所发生的事,由于它们勾起了我对往日的回忆,以致使它重现于梦中。但是,另一方面,我仍不能接受奥地利心理学家斯瓦伯达所说的“生物学意义上的规则时差”。他认为,在导致梦的印象的白天经历与梦中的复现之间,相差不会超出十八个小时。
目前,我只能说,我确信每个梦的刺激,都来自“他入睡之前的经验”。
艾里斯[6]对这问题也极感兴趣,而且曾费尽心血地想找出经验刺激与梦复现之间的时差,但也仍不能得到结论。他曾讲述过自己的梦:他梦见他在西班牙,想到一个叫达拉斯或瓦拉斯或扎拉斯的地方去。可是醒来后,他发觉他完全记不起有过这种地名,同时也不能由此联想出什么线索来。但若干个月后,他发现在由圣塞巴斯提安到毕尔巴鄂的铁路途中,确实有一个站叫扎拉斯,而这个旅行是他做这梦前8个月时进行的。
所以,最近所发生的印象(做梦当天则为特例),其实与很久之前发生过的印象,对梦的内容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要是那些早期的印象与做梦当天的某种刺激(最近的印象)能有连带关系,那么,梦的内容就能够包容一生各个时期所发生过的印象。
但到底为什么梦会那么侧重于最近的印象呢?如果我们用以前曾列举过的一个梦来做更为详尽的分析,或许能够获得某种结论。
有关植物学专论的梦
我写了一本有关某种植物的专论,这本书就搁在我面前。我翻到其中一页折皱的彩色图片,看见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如同植物标本收集簿里的一样,附夹在这一册之中。
解析
就在那天早上,我曾在某书店的玻璃橱窗内,看到一本标题为《樱草属》的书,这是一本有关樱草类植物的专论。
樱草花是我妻子最喜爱的花,她最高兴我回家时顺便买几朵给她。而令我最感遗憾的是,我极少记得买这花回来给她。由这送花的事,我联想到另一件最近我刚对一些朋友们提起的故事。我曾以此故事来证实我的理论——“我们时常出于潜意识的要求而忘掉某些事情,事实上,我们可由这遗忘的事实,追溯出此人内心不自觉的用意。”我所说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位年轻妻子,每年她生日时,她丈夫总会赠给她一束鲜花,而有一年,她丈夫竟把她的生日忘了,结果那天他妻子一见他空着手回到家,竟悲伤地啜泣起来。这位丈夫当时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待到他妻子说出“今天是我的生日”时,他才恍然大悟,拍着脑袋大叫“天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竟完全忘掉了!”而立即想出去买花。但她已伤心不已,并且坚持说她丈夫对她生日的遗忘,显然是已不再像往日那般爱她的铁证。而这位L女士两天前曾来过我家找我妻子,并且请她转告我,她现在身体已全部康复(她几年以前,曾接受过我的治疗)。
还有别的一些需补充的事实,我确实写过一篇关于植物学的专论,我所谈论的是有关古柯植物[7]的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引起了喀勒的兴趣,以致他发现了其中所含古柯碱的麻醉作用。当时,我曾预言古柯植物所含的类碱将来能够用在麻醉上,只遗憾自己未能继续研究下去。而做梦醒来的那个早上(那天早上太忙,我未能抽出时间对这梦作解析,直到当天晚上,才开始分析),我在一种所谓白日梦的状态下,曾想到古柯碱的问题,并且梦见我由于患了青光眼,而到柏林一位想不起姓名的朋友家中,请一位外科医师来给我开刀。这外科医生,并不知道我的身份,于是竭力鼓吹自从古柯碱问世以来,开刀变得如何如何方便,而我本人也不愿说出,关于这药物的发现自己曾是有功之臣。由于在梦幻里,我还考虑到一个医生要向他的同行索取诊疗费是何等尴尬的事。假若他不认识我,那我就不必像欠什么人情似的付帐给这柏林的眼科专家。但待到我清醒过来再回味这白日梦时,发觉这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回忆。在喀勒发现“古柯碱”不久之后,我父亲由于青光眼而接受我朋友——眼科专家柯尼斯坦的手术。当时喀勒亲自来负责古柯碱麻醉,而在手术室里,他曾说了一句话:“嘿!今天可将咱们这三位与发现古柯碱工作有关的家伙都聚到一块儿啦!”
现在,我的思绪又跳到最近一次令我想起古柯碱的场合。就在几天前,我收到一份叫《纪念刊》的刊物,这是由一些学生们为了感谢教师们和实验室的指导先生们的教导而集资印发的。刊物中,在每位教授的名位下均列出他们的重大著作及发现,而我一眼就看到他们将古柯碱的发现归功于喀勒的名下。现在我才明白,这个梦是与前一个晚上的经验有关。那天晚上,我送柯尼斯坦医师回家,在途中两人谈到某一话题。每当提起这话题,我就会感到非常兴奋。谈话甚为投机,甚至到了门廊,我俩仍站在那儿讨论不休。碰巧格尔特聂(Gartner)教授夫妇正要盛装外出,我曾礼貌地对他太太的花容玉貌恭维了几句,而我现在方想起,这位教授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份《纪念刊》的编者之一,也是因这次邂逅而导致了我的那些联想。此外还有我所提过的那位L夫人生日那天的失望,我与柯尼斯坦的谈话内容或许也与此有点关系。
我现在再对梦中另一成分作一下解释。“一片已脱水的植物标本”夹在那本学术专论的书里,并且看起来就像是一本“Herbarium(标本收集簿)”一般,而Herbarium使我联想到Gymnasium(德国高等学校)这个词。然后,我想起有一次我们高等学校的校长召集了高年级学生,要大家一同编一个高校的植物标本采集簿,避免学生只会死读书而不知实物与书本相结合。校长分配给我的工作很少,只不过是几页关于十字花科植物的而已。这令我感到,他似乎认为我是个帮不了多少忙的家伙。实际上我对植物学一向就不太爱好,记得入学考试时,在口试那一关,他曾考我有关标本的名字,而我就栽在这种十字花科植物的问题上。若不是靠着笔试拉回一些分数,我还真会考不上呢!十字花科其实就指菊科,而事实上我最喜欢的花——向日葵便属于菊科。我妻子,她可对我更为体贴,到市场买菜时,经常会为我买些这种我最喜欢的花回来。
“那本专论就摆在我面前”:这句话又引发我另一联想。昨天我的一位在柏林的朋友来信说:“我一直期待着你想写的有关‘梦的分析’的书能及早问世,仿佛你已大功告成,而那本大作就摆在我面前由我逐页拜读着。”噢!其实我自己更是盼望这本书真的已写完了,而能呈现在我面前呢!
“那折皱的彩色图片”:当我还是一名医科学生时,一门心思只想多读一些学术专论,虽说当时经济不甚宽裕,但我仍订阅了许多医学期刊,而其中所含的彩色图片,使我非常的喜爱。同时我也始终为我这种治学精神而自豪。当我开始自己写书,且须得为自己的内容作插图时,我记得就曾有一张画得极糟,以致曾受到一位同事的善意的揶揄。由此,我不知怎么又联想到我童年的一段经历。我父亲曾有一次不经意地递给我和妹妹一本内含彩色图片的书(一本叙述波斯旅游的画),而瞧着我们将它一页页地撕毁。这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实在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当时我仅有5岁,而我妹妹比我小两岁,可那时我们两个小孩子不懂事地把书一页页地撕毁(就像向日葵般片片地凋落)的印象,却极为深刻地存在于我的脑海里,后来我上了学便开始对收藏书籍产生疯狂的兴趣(这点有些类似我由于喜欢阅读学术专论而引起梦里那种有关十字花科与向日葵之类的内容),其疯狂程度堪用“书呆子”一词来形容。从此以后,我常常注意到我之所以如此疯狂,也许与我童年这段经历有关,换句话说,我认为是这段儿时的印象,导致了我日后收藏书籍的嗜好。当然,我也因此充分意识到我们早年的热情常常是在自找烦恼,因为当我16岁时,我就因此嗜好而欠了书商一笔几乎付不起的书资。当时,我父亲是不太赞成的,仅因为多看书是一种好嗜好,他才纵容我这样挥霍。但提到这段年轻时的经历,又使我联想到这正是我做梦的那天晚上与柯尼斯坦谈兴正浓时,他所指出的我的一大缺点——我这个人往往过分地沉浸于自己的嗜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