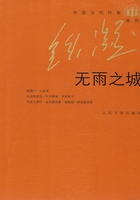
第5章
星期天早晨,陶又佳照例是不起床的。她裸着身子似睡非睡地躺着,思绪正如她此刻的身体:散漫而又自在。
五月的阳光透过亚麻窗帘洒向陶又佳的大床,她从床的这头滚向床的那头,接着双臂交叉搭住肩膀,就好像自己在搂抱自己。她搂抱着自己也不睁眼看表,揣测现在是上午十点钟,那么,她还可以继续在床上懒下去。
懒床是陶又佳的一种健身方式,这方式并非如常人的看法——是一种懒惰。陶又佳不懒,她精力充沛而且有些任性,每当朋友们批评她这种坏毛病时,她就搬出去年从美国探亲带回的美国经验:她的居住在纽约的小姨和她有着同样的懒床习惯,小姨把这习惯称为“做蔬菜”,也就是懒散地在家中闲躺一天,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好比没有思维的蔬菜那样。小姨就常在周末晚上给朋友打电话宣布第二天她要当一天“蔬菜”,请她们不要打搅她,然后在第二天,陶又佳便伙同着小姨开始她们一天的“蔬菜”生涯。她们怀着一点儿恶毒的愉悦不讲究姿态地倒在各自的床上睡过去,似乎以此来报复外面那个喧嚣的世界,又似乎制造这散漫无序的一天正是为了抖搂精神,容光焕发地迎接那个世界的喧嚣。充足的睡眠和全身彻底的放松使她们的皮肤新鲜而又富于弹性,她们痛快地淋浴,放开胃口大吃生菜沙拉和佛罗里达蜜橘。然后小姨郑重其事地嘱咐陶又佳,要她回国后坚持至少十天做一次“蔬菜”。说无论如何化妆品不能挽留女人的青春,只有充足的睡眠和放松的身心能够拯救女人的皮肤和脸色。小姨说她本人所以能够在纽约的节奏中保持着充满活力的仪容,就是得益于定期的蔬菜养生法。还说难道一定要去美容厅、健身房么?完全不一定!陶又佳马上接过小姨的话说,她就从来不做体育锻炼,因为她觉得那是一个负担而她又没有长性。人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做不愿做的事呢?她乐意懒床乐意做蔬菜并且在这定期的作为中获得了好处,干吗不坚持着做下去?这并不是女人的恶习,这实在是一个现代人面向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未来的一个科学而又现代的手段——不是么,生活节奏越快你越得懂得在什么时候、怎样使自己慢下来。是的,小姨马上说,时髦的不一定就是好的,你需要的才是最好的。
除了懒床,今日的陶又佳还需要什么?从前她需要结婚,于是她结了婚;后来她需要离婚,她就离了婚。当她离婚之后才发现自己还是这样地年轻,或者三十一岁,或者三十二岁,而旁人看她也许是二十五岁,也许是二十六岁。于是她暗地里庆幸她离婚离得是如此果决和利索,她常想或许她和前夫董达离婚的一切表面缘由都是假的,关键是她本来就不该同他结婚。那些表面的理由其实是有点可笑的,比如董达是陶又佳懒床习惯的最直接的反对者。他常在她这种养生过程中猛地掀开她的被子,让她的身子彻底裸露在他的眼前,然后拽住她的一条胳膊逼她起床。那时陶又佳气愤地扭着身子,把头拼命向后仰去好让它重新挨上枕头。他皱着眉头咬着牙,她晃着脑袋闭着眼;他一次又一次地拽她,她一次又一次地反抗。他们像一对正在扭打的仇敌,又好比一对制造扭打以创造激情的恋人。她常在这种较量的高潮中获得被人发着狠地疼爱的欣慰,他常在这种较量的高潮中体味她那带着蛮劲儿的裸体的美丽。他们最终会在“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拥抱在一起,就好像当初那一场忿忿的搏斗原本是为了此刻的做爱。之后她继续她的懒床,他呢?他就回到书房摆弄他的文字。他是一个作家,没有大红大紫过,倒也一直被读者记着。董达常想,他的作家生涯就像他和陶又佳的爱情——热热闹闹,不能算真,也不能算假。
陶又佳与董达离婚的另一个表面缘由,是董达因生病而发生的那么一次蜻蜓点水般的浪漫。他去医院割扁桃腺,手术后住院的几天里认识了一个小护士。她作为文学爱好者和他的崇拜者,给他以格外精心的照料,陪他在医院的桃树林里散步,听他侃文学听得眼泪汪汪,还定时去医院门口的冷饮店为他买来扁桃腺手术后应该多吃的雪糕、冰淇淋什么的。这使董达不断地想到,啊,人的一生千万不要有什么大病,但一定要隔长不短地生些小病。你不能说这些小病不是病,比如割扁桃腺,但它并没有妨碍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一切,你可以愉快地接受亲友的慰问,你可以在这期间对外面的一切不负责任,而且,你还有闲情逸致企盼着或者预感着一种无伤大雅的温情。住院部那特有的碘酊与来苏水的混合气味,那些抱着葡萄糖瓶子匆匆跑来跑去的白色身影对于重病者可能是昭示着灾难的救急,但对于生小病的人,这气味和身影给予他们的多半是惆怅的寂寥。人心在这时是脆弱的,人在这惆怅的寂寥之中最容易被哪怕是特别微小的一点温情所打动。董达被小护士打动过,经过她的通融他还住进了单间病房,病房里摆着小护士大清早为他采来的湿漉漉的波斯菊。后来董达向陶又佳承认,当时他已经可以出院了,但为了那个护士,他又在病房里多泡了几天。
陶又佳是通过小护士写给董达的一封短信才发现医院里的故事,那信中有这样的句子:“……亲爱的董老师,我不敢称呼您别的,但我却敢于在您智慧的双唇中间融化自己……”陶又佳把信看完还给了董达,然后和他谈起离婚的事,她并不是吃那个小护士的醋,她只是想到,一个随便就可以同护士发生恋情的男人,她又有什么必要和他过下去呢?也许她早就从骨子里瞧不起他了,医院的事情只不过是解除他们婚姻的一个契机。
他们离了婚,分手时董达对陶又佳说:“我没有想到你是这么不容我,又佳。你是这么不容我……”
陶又佳心中一惊。董达用了“不容”二字恰好点在了她的心上。为什么她会不容董达?事后她做过分析,她想那是因为在这场婚姻中她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她被动地接受着董达狂热的爱,他的文字也迷惑着她。她发现结婚时她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她不知道怎样爱她的男人,或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他,她只是习惯性地领略他给予她的狂热,她甚至以为那是应当应分的。在这场婚姻之中她究竟付出了什么呢?没有。她结过婚了可她还不知道爱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没有刻骨的痛楚就不可能有过真爱。
离了婚的陶又佳很轻松了一阵,她首先给她的密友丘晔打电话作了通报。丘晔来到陶又佳的家里,一进门陶又佳就说:“哎,这回你可以在我这里随便些了!你可以随便侃,还可以随便说脏话。”
“怎么叫脏话!操!”丘晔说。
“这还不叫脏话。”陶又佳说。
“这怎么能叫脏话?操!”丘晔大叫一声,和陶又佳分别笑倒在两只小沙发上。
丘晔比陶又佳大七八岁,是个颇有些经历的女人,父亲当过这省的副省长。她剪短发,专抽细支雪茄,说话带脏字。她声音低哑,但性格豪爽,认识许多上下人等。过去董达曾经很不喜欢陶又佳有这么一位满嘴脏话的朋友,丘晔每次来看陶又佳都得控制着自己,省掉话里的许多脏字。现在她不必再控制自己,她拉开冰箱自己找了一罐矿泉水,说:“我对作家一向就没有好感,操!”接着她又夸奖了陶又佳的好气色。
陶又佳坐在丘晔的对面说:“你知道你必须跟一个作家结过婚你才知道他们多么不值得你爱。”她的语气很超脱。
“可我没跟他们结过婚我也知道他们是多么没意思。”丘晔点燃雪茄,把火柴摇灭。
“是没意思。”陶又佳说,“他们的意思也许都写到瞎编的书里去了,待到他们自己生活的时候,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如董达,你别以为我真是因为那‘第三条腿’才跟他离婚,我发现他们这种人谈起社会、国家、民族的兴衰是那么的慷慨激昂,好像社会上到处是疮疤,官场里处处有罪恶,一切问题的解决惟有靠了他们手中那杆笔。要么就是他不屑于被中国人评论,他不屑于被外国人研究,他不屑于被某官员请吃饭……一百个不屑于。可是轮到自己的利益呢,一个个世俗得要命。董达评职称的时候就求我到市职改办一个处长那儿给他要指标。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佳你是记者什么人都认识,不像我,整天坐在家里码字,难道你真的不乐意用那么小小的一点青春朝气为你的丈夫赢得他该得的利益么?”
“哟,还挺肉麻的。”丘晔说。
“关键不在于他的肉麻,在于他求我时先把我贬成一个会利用青春朝气的什么人都认识的人,而他自己则是为了事业清高之极。于是为了他的继续清高,也因为我本来不清高,理所当然得由我出面为他要指标。”
“我倒觉得这并不是主要的,”丘晔富有经验地看着陶又佳,“关键在于你不爱你的丈夫。假如你真的爱他,像评职称这种小小的世俗又算得了什么?古今中外从伟人到平民,谁他妈不世俗?更何况一个中国的穷作家。关键是你不爱你的丈夫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妥协——我是指那种精神上的真正妥协。”
“我承认我不爱他,”陶又佳说,“但你不能不承认通过他我的确看到了中国一些作家的弊病。”
“这我同意。”丘晔说,“那些男作家专爱倾听女性的不幸或者向女性倾诉不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有她们。”
“那些女作家呢?”陶又佳说,“不是孤芳自赏假装天真,就是口出狂言作傲慢状,再不就是神志不清词句混乱以疯卖疯。”
丘晔笑起来。陶又佳等她笑完接着说:“还有他们对待普通家务事是那么的没有本领,董达连日光灯上的起辉器坏了都不会换,他甚至不能把一颗钉子顺利地钉进墙里去。可是那些工人是怎么干活儿的?那年有几个工人来给我们安装空调,一个小伙子蹲在地上手持斧子把一块木头砍成许多楔子。他的一双大手是那样粗糙,可是它们砍起楔子来是那么灵活,那些木块儿在他手下活蹦乱跳,他简直不是在砍,他是在引逗木楔子跳舞。就这么点事,简直能叫你眼花缭乱。”
“当时你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感觉?”丘晔问。
“我不知道,我说不清楚。”
“是敬佩?”
“不是。”
“是好感?”
“也不完全。”
“是性欲?”
“当然不是!”陶又佳停顿了一会儿,说:“我想可能是冲动,一种生命要生活的冲动。”
……
懒床的陶又佳就在生命要生活的冲动之中彻底睁开了眼。在这套董达留下的房子里,在这张她与董达离婚后重新购置的大床上,结婚的痕迹越来越淡漠,淡漠到她常常忘记她结过婚。只因她已不再寂寞,只因她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生活。是的,她懒散,她在爱。
她掀开身上的毛巾被,就那么光着身子在房间、在厨房、在过厅里走来走去。这本是她做姑娘时的一个恶作剧似的习惯,她愿意不穿衣服跑到镜子前一闪一闪地看自己。结婚以后她把它改掉了。现在她又把这习惯恢复了起来。她常常为她的身体感到骄傲,她觉得这个身体无愧于世上任何一种看见它的东西。她喜欢它清新、干净,她愿意让微风和自然的空气吹拂在这个身体之上,让光和影直接地照耀它也掩映它。
过厅里的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眼睛却望着电话桌旁穿衣镜中的那个裸体:“喂……什么?”她提起话机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她听见了一个遥远而又动人的声音,一个意外的然而她永远等待的声音。
“你在什么地方?”她对着电话说。
“香港?我以为你回来了。”她对着电话说。
“是的,没有想到。”她说。
“我知道。”她说。
“在国内你不敢这样跟我说话。”她说。
“你猜得对。”她说。
“嗯,光着。”她对着话筒笑了。
“我也是。”她说。
“我也想。”她说。
“特别特别想。”她说。
“心疼,疼极了。”她说。
“你要少吸烟。”她说。
“我爱你,真的。”她说。
“我不再说,我已经说好几遍了。”她说。
“什么?”她说。
“是的,我是你的我等你。”她说。
“我知道你们会顺利。”她说。
“好。”她说。
“什么也没吃。”她说。
“是晴天。”她说。
“我真的爱你我要你!”她说。
“……”
她久久地攥着话筒就像攥着一个渴望贴近的生命。
她和他并没有约好打电话,但是他打来了,他的一个电话足够她快乐好几天。她跑进卫生间放水,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陶又佳的母亲。她告诉陶又佳,舅舅来了,要她过去吃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