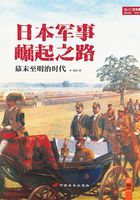
第3章 江户日本(2)
经历丰臣侵朝战争惨败的日本人何以保持如此满溢的自信?只因战国时代以来,陆续乘船来此的西洋人确实让日本人开了眼界。1579年,日本天主教耶稣会负责者葡萄牙人范礼安(A.Valignano)与九州基督教大名大友宗麟合作,派遣天正遣使团(团员都是十三四岁的少年)访问欧洲,拜见罗马教皇。1613年,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派遣的庆长使节团,更是乘坐500吨级的西班牙式大帆船桑帆号(由西班牙人指导建造),向西跨越太平洋至美洲墨西哥,再渡大西洋至欧洲游历。这两,支使团回国时,都恰逢日本掀起排斥基督教运动,使得这些见识非凡的团员无法施展抱负。但毕竟日本对整个世界已经持有基本认识,而西洋人诸如“这个国家的人是我迄今发现的国家中最高级的,比日本人更优秀的民族在异教徒中恐怕找不到”(首位来到日本的传教士沙勿略语)之类的评语,使日本人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拿来与中国、朝鲜一起评价,而且还胜出了!其洋洋自得自是理所当然。在日文版的“亚细亚洲”地图上,日本人首次将本国国名标为——大日本。水户德川家的一代明君德川光圀,设立彰考馆编撰鸿篇巨制《大日本史》,经250年岁月才在1906年正式完成402卷的恢弘伟业。其书遵循朱子学史观,尊“万世一系”天皇皇统,由此形成的所谓“水户学”,将对幕末尊皇论思想,以至于“大日本帝国”的最终建立,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历数次大规模迫害天主教浪潮(以“岛原天草之乱”于1638年遭幕府军血腥镇压为标志)的日本,在出岛口岸成功设置、沿海警备体制确立之后,正式进入锁国状态。在当时东亚范围内,清朝与朝鲜等同样锁国,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西方殖民者的步伐越来越快,已将远至东南亚的广大区域占为殖民地,为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所需的财富与原料,进行残忍的殖民掠夺。他们所带来的完全异样的技术、经济与文化的冲击,以及更加令人骇异的“吉利支丹”教(日本对葡萄牙语基督教徒“Crist?o”的音译,但至江户中期便被蔑称为“鬼理死丹”之类),在一个战火纷飞、须借助一切先进战争技术的时代犹可容忍,但在已实现统一与和平的东亚农业社会中,则是万万不可忍的。东亚各国均有此共识,无甚区别。
正如清朝锁国并没有影响宫廷获得制造精巧的西洋钟表、聘请西洋画师,并在南方设立口岸、授权商行贸易一样,日本锁国同样没有影响大名、武士及庶民对外国的学习热情。而且与清朝和西洋的接触基本只局限宫廷与贸易口岸,平民百姓和文人士大夫基本无交集这种情况不同,日本出现了在社会上进行广泛活动的“兰学者”(由于江户时代日本对欧洲人只能接触到出岛的荷兰人,因此由荷兰人介绍的各国知识一律被称为“兰学”)。兰学的主体是西方医学,其标志性成果是1774年兰学者杉田玄白、前野良泽等根据荷兰医书译编而成《解体新书》,此前山胁东洋和小衫玄适已进行了日本首例医学人体解剖(1754年)。
兰学扩展必然涉及军事学领域,其标志性成果是林子平著于1792年的《海国兵谈》。在此之前,日本林林总总的所谓兵法书,只论及日本国内战争,而以兰学为基础的《海国兵谈》则以日本作为世界海洋中一个岛国的视角,提倡日本须拥有一支较为现代化的海军,须在全国建设沿岸炮台,而强大海军的出现则需要强化幕府中央权力并提高经济实力,否则不能击退外部势力的攻击。《海国兵谈》问世后不久便遭遇幕府打压西方学术的逆流,因此对当时日本的对外防御政策无甚影响,但幕末时期其影响力将会慢慢显现而出。
幕府之腐败
江户日本出现了一批颇有活力的兰学者,说来虽然有些奇怪,但大抵要归功于看似非常落后的幕藩世袭制。在幕藩制度下,士农工商阶层牢牢固定,所有人的社会地位都是世袭的,只有身具德川家康亲缘血脉之人才能出任将军,家老如此,大名如此,藩士如此,以至于下层武士、农民、商人亦皆如此,代代世袭。而大海对面的清朝实行的是看似开明的科举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举谋取官职,结果使得全民热衷于毫无用处的八股文。江户日本没有全国性科举(但存在针对藩士的局部性考试),那百姓还有什么向上发展的出路呢?只能去做学问,而且必须是不务虚、讲实际,能学以致用、赚得真金白银的学问。这正是兰学产生的源泉所在,也能说明兰学为何以医学知识作为主体——因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医师总是衣食无忧的。不仅如此,日本全国到处都有寺子屋,教习小孩学假名、汉字、书法、算盘和地理等,竟使日本成为19世纪全世界平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幕末统计庶民阶层男子识字率54%,女子20%,而武士阶级则达到100%)。藩士子弟则进入各藩的藩校就读,这里倒有些死板教育的流毒,学生不问意义地死记硬背四书等儒学经典译书,考试成绩不佳甚或影响到继承家业。不过,待子弟成长为青年后,又须进行传统的武艺学习(剑术、枪术、柔术、弓术、炮术、马术等),江户后期更加入了技术性的兰学知识。总体来说,江户日本拥有极好的普及教育基础,较之清朝的教育更具实用性倾向。
但引进西学、教育普及与武士忠诚尚武等等元素,只能作为未来日本开拓进取的铺垫,而在江户盛世时期,社会却不可避免地陷入发展停滞的泥沼。过分强调实用性原则与世袭制,亦意味着缺乏强烈外部刺激的情况下,无人愿意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尝试,只以修修补补来应付问题。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于公元1680年继位后,一度励精图治,但自元禄(此年号开始于1688年)起渐渐耽于政务,幕府权力核心人物柳泽吉保等人大搞面子工程,同时大肆贪污受贿。将军在干什么呢?德川纲吉颁布了《生类怜悯令》,最初是禁止舍弃病牛病马,到后来竟然连苍蝇、蚊子都不准杀,大名必须把狗放入轿中往来运送,百姓每次都要对着狗轿子跪拜,不无讽刺地敬称狗为“犬大人”——这是基本停滞的社会中,大权在握却受僵化体制所限无事可做的统治者才会想出来的歪主意,与明朝万历皇帝“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相映成趣。
并非偶然的是,江户元禄时代和明朝万历年间一样,尽管政治混乱无序,经济泡沫膨胀又破灭,但社会文化却极度繁荣。我们今日熟知的许多日本传统文化符号,如妇女在和服上绑纷繁复杂的带子,榻榻米不是只坐一席而是铺满整个房间等等,都自元禄时代兴盛。面对深重弊端,第六代将军德川家宣推行“正德之治”(主要进行策划指挥的是新井白石,此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著有《西洋纪闻》、《藩翰谱》、《本朝军器考》等),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采取选拔能吏、开发新田、稳定米价、统一货币、管制工商业等许多措施,而最知名的举措便是设置目安箱(意见箱)。幕府政治似乎是脱胎换骨了,通过《俭约令》的贯彻,幕府与各藩严峻的财政状况亦大为改善。
然而,与古今中外无数成例类似,如此不触及根本,只由“明君贤臣”推行一时的改革,必然只具一时之功效。至18世纪中叶,四海升平之下幕府政纪又松弛至极点,贪污腐化已成为无可质疑的惯例。例如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幕下掌握大权者,老中田沼意次便公然执行贿赂政治,想要在幕府中混个官职,就必须向其行贿。据说田沼意次只要回到家里,看到堆积如山的财物,登时就会喜上眉梢。幕府的统治已病入膏肓,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尽管武士身份仍被尊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但由于普遍的贫困化、顶替服役现象,武士阶级的战斗力已经下降到惨不忍睹的境地,只不过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揭露这一点而已。武士的贫困化,实因天下承平日久,负管理职责而不知具体生产艰辛的武士家族都变得人丁庞大又碍于面子讲究排场,一旦由俭入奢,债务便如滚雪球一般膨胀直至破产。破产武士不得不拿出不动产、传家宝,以至于武器、盔甲和马具等,典当给商人以换得金钱。
如此这般,本应处于社会两极的武士、商人立场颠倒。武士将服役的权力也按“株”论价,租卖与商人,使商人得以全副武士派头招摇过市,而家主亦不反对。渐渐的,封建主从关系演变成为雇佣关系。江户中期的儒学思想家荻生徂徠在其著书中感叹道:“近来顶替服役之风盛行,诸侯已无世袭家臣矣。”此话虽略显夸张,却也反应了现实之严峻。任何稍具远虑之人都可想见:商人花钱替武士服役,只是为了扭转自身社会地位,却腐蚀了日本武士军制。太平盛世自是无妨,万一有敌入侵,商人纷纷退走,无用武之地,而武士们平日醉生梦死,不是搞众道(同性恋)就是与妓女殉情(即所谓“心中”,擅长描绘此题材的近松门右卫门著有《曾根崎心中》、《心中天网岛》等风靡至今的作品),显而易见也是指望不上的。出路何在?荻生徂徠在所著《政谈》中便热烈主张“恢复旧日农兵”,水户藩德川光圀甚至付诸实践,令家臣的儿子们除长子以外,都下乡去耕地。其结果自然是完全失败,恢复农兵沦为空谈。
幕藩封建主从制度,是建立在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以来苦心营建的兵农分离制度之上的。如果武士们又都被逼回乡下去种田,结成乡野武士团,那只能导致他们不服幕府权威,为了争夺土地而大打出手,最终导致战国乱世再临。荻生徂徠所设想的武士下乡之后将重归淳朴,努力耕地、训练,为幕府出力,纯属儒家学者的幻想。当然,如果19世纪中叶西方人并没有打开日本国门,而幕府统治一步步腐化下去直至彻底崩溃,那么武士重返乡间乱战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但如此假设历史并无意义,事实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来了,而日本武士将借机冲向海外。
武士之刃
江户时代,日本武士军队的武器装备及战术思想,仍停滞在战国时代末期,有些方面甚或倒退。但日本人对其武士军队的战斗力,却长期抱有天下第一的优越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及西洋国家进行对比时都自叹不如,却唯独在军事领域,如上文述及兵学家山鹿素行的言论那样,始终保持着非同一般的自信。当西洋坚船利炮终于在19世纪中期,轻松将东亚诸国大门一一撞开时,清朝犹自觉得礼教立国不能丢,朝鲜坚持“事大主义”以求平安,唯独日本被惊吓得全国上下鸡飞狗跳——只因日本自信之源泉犹如肥皂泡般被戳破了。日本武士是手持何物迎向西洋人的呢?让我们首先从冷兵器谈起。
提起日本冷兵器,首先想到的便是武士刀。武士刀制造技术精湛、外形冷峻美艳,堪称世界冷兵器王冠上的一颗明珠。但日本刀与武士这一身份紧密结合在一起,却是很晚才发生的事。古代日本虽从中国引入制刀技术(即“唐样大刀”),但当时日本武士却是以“骑射”为主要作战形式,“马上打刀”或者干脆下马持刀作战,并不常见——这要归因于早期武士大多有贵族背景,他们之间的战斗带有一些体育竞技的意味(比如交手前首先要互报家门)。随着时代的发展,武士阶层越发乡土化,他们之间的战斗褪去“骑射”华丽表演的成分,开始深入追求杀伤力和易用性。如此,日本发展出的太刀、打刀、胁差(中刀)、短刀、薙刀、枪等刃物冷兵器可以统称为“日本刀”,在当时也并不一定与武士身份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