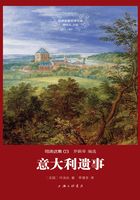
卡司特卢 的女修道院院长
的女修道院院长
一
险剧 经常让我们看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还有许多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也拿他们作为谈话资料,结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他们持有的不正确的见解。说起这些强盗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继承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残暴政权的反对党。新僭主通常就是灭亡了的共和国的最富裕的市民,为了笼络小民起见,他给城市点缀上一些辉煌的教堂和美丽的图画。例如腊万纳的波伦提尼、法恩擦的曼夫赖狄、伊莫拉的芮阿理欧、维罗纳的卡奈、博洛尼的奔提渥里欧、米兰的维斯困提,还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可以说是其中最不好战和最伪善的了
经常让我们看到十六世纪的意大利强盗,还有许多人对他们一无所知,也拿他们作为谈话资料,结果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对他们持有的不正确的见解。说起这些强盗来,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是继承中世纪意大利各共和国的残暴政权的反对党。新僭主通常就是灭亡了的共和国的最富裕的市民,为了笼络小民起见,他给城市点缀上一些辉煌的教堂和美丽的图画。例如腊万纳的波伦提尼、法恩擦的曼夫赖狄、伊莫拉的芮阿理欧、维罗纳的卡奈、博洛尼的奔提渥里欧、米兰的维斯困提,还有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可以说是其中最不好战和最伪善的了 。这些小僭主,惴惴不安,布置下了不计其数的毒杀、暗杀事件,而这些小国的史家却没有一个敢记述下来,因为这些严肃的史家都接受了他们的俸禄。想想每一个僭主不但直接认识每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知道这些共和党人都痛恨自己(例如托斯卡纳的大公爵考麦,就认识斯特洛奇
。这些小僭主,惴惴不安,布置下了不计其数的毒杀、暗杀事件,而这些小国的史家却没有一个敢记述下来,因为这些严肃的史家都接受了他们的俸禄。想想每一个僭主不但直接认识每一个共和党人,而且还知道这些共和党人都痛恨自己(例如托斯卡纳的大公爵考麦,就认识斯特洛奇 ),再想想这些僭主有好几个就不得善终,你就会明白,使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有大量才情和勇敢,使他们的艺术家有无比天才的仇恨是多么深,疑心是多么重。你也就看得出来这些强烈的激情多么妨害那种相当可笑的偏见的形成。在塞维涅夫人
),再想想这些僭主有好几个就不得善终,你就会明白,使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有大量才情和勇敢,使他们的艺术家有无比天才的仇恨是多么深,疑心是多么重。你也就看得出来这些强烈的激情多么妨害那种相当可笑的偏见的形成。在塞维涅夫人 时代,人们把这种偏见叫作荣誉,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子民
时代,人们把这种偏见叫作荣誉,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子民 ,所以应该牺牲性命,为主效忠;还有就是讨贵妇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只能依靠战场上或者决斗里的骁勇剽悍,才会在法国得到别人的仰慕,才会表现他的活动和他的真正才能;因为妇女喜爱骁勇剽悍,特别是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她们就变成了评定男人优劣的最高裁判。这样一来,向妇女献媚的精神就出现了。为了我们人人服从的虚荣心——这位残酷的僭主的利益,这种精神准备一个又一个地消灭了所有的激情,甚至于爱情
,所以应该牺牲性命,为主效忠;还有就是讨贵妇人们的欢心。在十六世纪,一个男人只能依靠战场上或者决斗里的骁勇剽悍,才会在法国得到别人的仰慕,才会表现他的活动和他的真正才能;因为妇女喜爱骁勇剽悍,特别是那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她们就变成了评定男人优劣的最高裁判。这样一来,向妇女献媚的精神就出现了。为了我们人人服从的虚荣心——这位残酷的僭主的利益,这种精神准备一个又一个地消灭了所有的激情,甚至于爱情 。国王们保护虚荣心,而且理由十足,结局就成了滥发绶章。
。国王们保护虚荣心,而且理由十足,结局就成了滥发绶章。
在意大利,一个男人可以靠各种才能成名:舞剑、发现古代写本,都能使他出人头地。看一下彼特拉克 、他那时代的偶像,你就明白了;一个十六世纪的妇女,爱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不但不下于一位武功彪炳的名人,而且还会远过于他。我们在这期间看见的是激情,不是向妇女献媚的习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这种情形正好说明为什么在意大利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柯勒乔
、他那时代的偶像,你就明白了;一个十六世纪的妇女,爱一位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不但不下于一位武功彪炳的名人,而且还会远过于他。我们在这期间看见的是激情,不是向妇女献媚的习惯。意大利和法国之间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这种情形正好说明为什么在意大利诞生了许许多多的拉斐尔、乔尔乔涅、提香、柯勒乔 ,而法国却产生了所有那些十六世纪的勇敢的统领,他们今天尽管默默无闻,当年却也杀死过成批的敌人。
,而法国却产生了所有那些十六世纪的勇敢的统领,他们今天尽管默默无闻,当年却也杀死过成批的敌人。
我请求大家原谅这些率直的真情实话。总之,由于中世纪意大利这些小僭主的残暴而又必需的报仇行径,人心反而向着强盗。强盗偷马、偷麦子、偷钱,一句话,偷一切生活上的必需品,大家是恨他们的;然而事实上,人心却向着他们。年轻的男孩子,鲁莽灭裂,惹下什么乱子,一辈子有这么一回,不得不“落草”(andar alla machia),就是说,逃进树林子,受强盗庇护,村里的姑娘们看上眼的是他,并不是别人。
今天,我们人人肯定还是害怕遇见强盗的;可是他们受了刑罚,人人又都可怜他们了。原因是意大利人民,非常机灵狡诈,顶爱嘲弄别人,一面取笑所有经过检查后发表的著作,一面经常在读那些热情地演述最知名的强盗的生平的小诗。他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的轰轰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一直活在下层社会里的艺术神经,何况官方对某些人的颂词,他们早就听腻了,所以这一类颂词,只要没有官方气味,马上就中他们的意。我们应当知道,下等人在意大利受到的某些痛苦,旅客即使在当地住上十年,也永远不会感到的。例如十五年前,在政府都想不出办法来清剿盗匪之前 ,他们吊民伐罪,惩治小城市的统治者,并不少见。这些统治者是一些月薪不过二十埃居
,他们吊民伐罪,惩治小城市的统治者,并不少见。这些统治者是一些月薪不过二十埃居 的专横官僚,自然对当地最有声望的家族唯命是听,而这些望族就靠这种极简单的方法,压制它的仇人。强盗惩治这些暴戾的小统治者,不见得就常常成功,不过,至少,强盗小看他们,敢于向他们挑衅,在这些有才情的人民看来,就不简单了。他们的种种苦难,一首十四行的讽刺诗就使他们得到了安慰,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一次羞辱。这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的专横官僚,自然对当地最有声望的家族唯命是听,而这些望族就靠这种极简单的方法,压制它的仇人。强盗惩治这些暴戾的小统治者,不见得就常常成功,不过,至少,强盗小看他们,敢于向他们挑衅,在这些有才情的人民看来,就不简单了。他们的种种苦难,一首十四行的讽刺诗就使他们得到了安慰,但他们永远也忘不掉一次羞辱。这是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之间的另一个重大区别。
在十六世纪,一个可怜的居民变成了大户人家的死对头,镇长判他死刑,人们就时常看见强盗攻打监狱,企图把受害者救出去。另一方面,有势力的家族也不太信任政府派去守卫监狱的八个或者十个兵,而是出钱招募一队所谓“布辣维” 的临时兵,驻在监狱周围,负责把可怜人押解到法场;他的死是行贿的结果。这个有势力的家族如果自己有一个年轻人的话,就由他充当这些临时编凑的兵的头目。
的临时兵,驻在监狱周围,负责把可怜人押解到法场;他的死是行贿的结果。这个有势力的家族如果自己有一个年轻人的话,就由他充当这些临时编凑的兵的头目。
这种风俗习惯使道德败坏,我同意;今天情形却不同了。我们有决斗,有苦闷,而法官也不出卖良心;不过十六世纪这些习俗,对制造名副其实的好汉,倒也万分相宜。
将近一五五〇年的时候,这种情形培养出来一些极其伟大的性格,可是今天还被各学院陈陈相因的著述所誉扬的许多史家,却在设法隐瞒这种情形。他们在世期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费拉拉的艾斯太家族、那不勒斯的各任总督,等等 ,以力之所能及的种种荣誉来酬谢他们的审慎的谎话。一个叫作吉阿闹奈的可怜的史家,打算掀开黑幕的一角;然而由于他敢说出来的,只是真情实况的极小的一部分,用的还是表示怀疑和暧昧的形式,读起来很不痛快,可是仍然免不了在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死在监狱里。
,以力之所能及的种种荣誉来酬谢他们的审慎的谎话。一个叫作吉阿闹奈的可怜的史家,打算掀开黑幕的一角;然而由于他敢说出来的,只是真情实况的极小的一部分,用的还是表示怀疑和暧昧的形式,读起来很不痛快,可是仍然免不了在一七五八年三月七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死在监狱里。
所以你想知道意大利历史,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不读那些被人同声赞美的作家的著作;你所见到的谎话的标价,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标得更高的;谎话的卖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要得更多的;买价在过去,也没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出得更多的。
在九世纪大乱之后,人们在意大利写的最早的历史已经提到强盗了,而且说起他们来,像是古已有之。(参看穆拉陶理的辑录 。)中世纪各共和国一被推翻(对艺术说来,是有利的,可是对公众的福利、正义和良好的政府说来,却是不幸的),最刚强的共和党人,比大多数同胞更爱自由,就逃进了树林子。人民受尽巴里奥尼、马拉太斯塔
。)中世纪各共和国一被推翻(对艺术说来,是有利的,可是对公众的福利、正义和良好的政府说来,却是不幸的),最刚强的共和党人,比大多数同胞更爱自由,就逃进了树林子。人民受尽巴里奥尼、马拉太斯塔 、美第奇等家族的欺凌,自然而然,就敬爱他们的仇敌了。继第一批篡夺者之后而掌握政权的那些小僭主,都像佛罗伦萨第一位大公爵考麦那样残酷(他派人暗杀逃到威尼斯,甚至于逃到巴黎的共和党人)
、美第奇等家族的欺凌,自然而然,就敬爱他们的仇敌了。继第一批篡夺者之后而掌握政权的那些小僭主,都像佛罗伦萨第一位大公爵考麦那样残酷(他派人暗杀逃到威尼斯,甚至于逃到巴黎的共和党人) ,给这些强盗添了好些新伙伴。远的不说,单只我们女主人公活着的那些年月,将近一五五〇年,孟太·马里阿诺公爵、阿耳奉扫·皮考劳米尼和马尔考·夏拉
,给这些强盗添了好些新伙伴。远的不说,单只我们女主人公活着的那些年月,将近一五五〇年,孟太·马里阿诺公爵、阿耳奉扫·皮考劳米尼和马尔考·夏拉 ,就在阿耳巴诺附近,成功地指挥着几支武装队伍,向当时极其勇敢的教皇的兵士挑衅。人民到今天还在仰慕这些著名的首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波河和腊万纳沼泽地,一直扩展到当年覆盖维苏威火山的树林。夏拉的大本营就在法焦拉森林,离罗马二十二公里有余,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由于他们的战绩,这座森林出了大名。在教皇格莱格瓦十三
,就在阿耳巴诺附近,成功地指挥着几支武装队伍,向当时极其勇敢的教皇的兵士挑衅。人民到今天还在仰慕这些著名的首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波河和腊万纳沼泽地,一直扩展到当年覆盖维苏威火山的树林。夏拉的大本营就在法焦拉森林,离罗马二十二公里有余,在去那不勒斯的大路上,由于他们的战绩,这座森林出了大名。在教皇格莱格瓦十三 在位期间,夏拉有时候啸聚到好几千人马。在今天这一代人的眼里,这位有名的强盗的详细历史是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大家从来不想了解他的行动的动机。也只是在一五九二年,他才被打败。他一看大势已去,就和威尼斯共和国进行谈判,带着他的最忠心或者最有罪(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的人马,向它投效。威尼斯和夏拉虽然有约在前,可是迫于罗马的要求,派人把他暗杀了,让他的勇敢的人马到干地亚岛
在位期间,夏拉有时候啸聚到好几千人马。在今天这一代人的眼里,这位有名的强盗的详细历史是难以置信的,原因是大家从来不想了解他的行动的动机。也只是在一五九二年,他才被打败。他一看大势已去,就和威尼斯共和国进行谈判,带着他的最忠心或者最有罪(你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好了)的人马,向它投效。威尼斯和夏拉虽然有约在前,可是迫于罗马的要求,派人把他暗杀了,让他的勇敢的人马到干地亚岛 去防御土耳其人。但是威尼斯消息灵通,知道危险的鼠疫正在干地亚流行,所以夏拉带到共和国效命的五百人马,不几天工夫,就剩下六十七名了。
去防御土耳其人。但是威尼斯消息灵通,知道危险的鼠疫正在干地亚流行,所以夏拉带到共和国效命的五百人马,不几天工夫,就剩下六十七名了。
这座法焦拉森林,是马尔考·夏拉作战的最后舞台。参天的大树盖着一座旧火山。每一个旅客将告诉你,这里是那引人入胜的罗马郊野的最壮丽的景色,沉郁的风貌像是为了悲剧才有的。黑黝黝的绿冕戴在阿耳巴诺山的峰顶。
远在有史以前,还在罗马创建许多世纪之前的一个时期,有一次火山爆发,在延伸在海和亚平宁山脉之间的辽阔平原的中心,涌起了这座壮丽的大山。卡维峰是它的最高点,周围就是法焦拉森林的沉郁的树荫,人无论站在什么地点,特拉契纳和奥斯西亚,罗马和提沃利,都望得见卡维峰;如今布满了府第的阿耳巴诺大山,正好在朝南的方向,成为那旅客赞不绝口的罗马天边的终点。峰顶原先有一所打击者朱庇特庙 ,拉丁各部族来到这里一同献祭,以一种宗教联盟的方式加强联系,现在改成了黑衣修士
,拉丁各部族来到这里一同献祭,以一种宗教联盟的方式加强联系,现在改成了黑衣修士 的修道院。旅客走在壮丽的栗子树的阴影底下,不几小时,就来到那些说明朱庇特庙遗址的大石块前头;这些沉郁的树荫,在这地方虽说可爱,但是旅客走在底下,望着森林的深处,甚至于在今天,心神依然不宁:他怕遇见强盗啊!他上到峰顶,在庙的遗址里,点起火来烧饭。他站在这控制罗马四郊的顶点,望见西边的海,虽说有十几公里远,可他觉得好像只隔两步;他辨识得出顶小的船只,他用最小的望远镜,数得出驶往那不勒斯的轮船的乘客。任何方向都是一片壮丽的平原,东边的终点是横在帕莱斯特里纳上空的亚平宁山,北边的终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别的大建筑物。卡维峰不算怎么高
的修道院。旅客走在壮丽的栗子树的阴影底下,不几小时,就来到那些说明朱庇特庙遗址的大石块前头;这些沉郁的树荫,在这地方虽说可爱,但是旅客走在底下,望着森林的深处,甚至于在今天,心神依然不宁:他怕遇见强盗啊!他上到峰顶,在庙的遗址里,点起火来烧饭。他站在这控制罗马四郊的顶点,望见西边的海,虽说有十几公里远,可他觉得好像只隔两步;他辨识得出顶小的船只,他用最小的望远镜,数得出驶往那不勒斯的轮船的乘客。任何方向都是一片壮丽的平原,东边的终点是横在帕莱斯特里纳上空的亚平宁山,北边的终点是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别的大建筑物。卡维峰不算怎么高 ,人用不着历史解说,就能把这卓绝境地的任何细枝末节辨别出来,可是在平原或者在山坡望见的每一丛树林、每一堵断墙,都又让人想起提图·李维
,人用不着历史解说,就能把这卓绝境地的任何细枝末节辨别出来,可是在平原或者在山坡望见的每一丛树林、每一堵断墙,都又让人想起提图·李维 说起的一场以爱国精神和骁勇剽悍著称的惊人战役。
说起的一场以爱国精神和骁勇剽悍著称的惊人战役。
我们今天还可以沿着早年罗马君王走过的凯旋路,来到打击者朱庇特庙遗留下来的大石块前头;黑衣修士的花园的墙就是拿它们垒起来的。路面铺着修得很整齐的石头;我们在法焦拉森林中间,还看得见这样一长段一长段的路。
熄灭了的火山口,现在盛满一汪清水,变成周围有十一二公里大小的秀丽的阿耳巴诺湖,深深嵌在火山喷出来的岩石里面。湖边是罗马的老城阿耳柏,从最早的国王们那时起,就根据罗马政策把它拆除了。 不过它的遗址还在。若干世纪以后,离阿耳柏一公里远近,现代的城阿耳巴诺在面向海的山坡上兴建起来。可是一道石头帷幕,隔开了湖和城,谁也望不见谁。从平原望过去,在强盗疼爱和经常被人赞扬的森林的又浓又黑的绿颜色上面,城的白颜色建筑显得更白,同时森林从四面八方兜过来,王冕似的盖着火山。
不过它的遗址还在。若干世纪以后,离阿耳柏一公里远近,现代的城阿耳巴诺在面向海的山坡上兴建起来。可是一道石头帷幕,隔开了湖和城,谁也望不见谁。从平原望过去,在强盗疼爱和经常被人赞扬的森林的又浓又黑的绿颜色上面,城的白颜色建筑显得更白,同时森林从四面八方兜过来,王冕似的盖着火山。
阿耳巴诺今天有五六千居民,一五〇四年,还不到三千,在头等贵族中间,当时正兴旺的是有势力的家族堪皮赖阿里,我们下文就要演述这一家人的苦难。
这个故事是我从两部很厚的写本译出来的,一部是罗马写本,一部是佛罗伦萨写本。它们的风格接近我们的古老传统的风格。我不怕失败,斗胆把这种风格移植过来了。现下十分优雅和匀整的风格,在我看来,和以上所述,特别是和两位作者的议论,太不协调。他们是在将近一五九八年的时候写的。我恳请读者宽容他们,并宽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