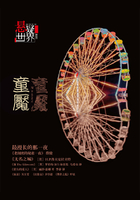
第7章 老闺密的秘密一夜(4)
但是,爸爸妈妈都要上班,像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孩子,通常都交给老人来带。因此,我的大多数童年,都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恰好我也是他们唯一的外孙。许多个傍晚,爸爸将我放在自行车书包架上,骑过苏州河边,穿过老闸桥,从条小巷子,进入天潼路799弄。那条弄堂地下铺着石板,小时候丝毫不觉得狭窄逼仄,因为在小孩眼里一切都是大的。外公外婆就住在59号的过街楼上,穿过一道陡峭狭窄的木头楼梯,就到了时常散发着白兰花香气的房间。透过地板下的缝隙,可以看到底下的门洞。我特别喜欢爬上小阁楼,趴在屋顶突出的“老虎窗”边,原来那块狭窄的长方形的蓝色天空,一下子变得如此辽阔。眼底是大片的黑色瓦楞,偶尔长着青色野草,再远望仍是层层叠叠的瓦片,头顶不时飞过邻家养的大队鸽子……那时最爱看《聪明的一休》,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那个挂在屋檐下布扎的小白人。我常在黄梅天的雨季,趴在阁楼的老虎窗里,看着密集的雨点落在窗上,看着阴沉的天空乌云密布,幻想屋檐下也有个小白人随风飘舞,全世界都在风雨中寒冷发抖——后来特别喜欢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不仅因为大师与我同名,更因为电影里那个城堡式的亭台楼阁的世界,那些高悬于墙面的窗户都像极了我的小阁楼。
而我就读过的第一个小学,也在天潼路799弄的尽头,几乎紧挨着苏州河,是闸北区北苏州路小学。那个校舍可是个老洋房,妈妈给我报了个美术班,也在这所小学,叫菲菲艺术学校,可惜我不能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阁楼画出来了。
我一直在想,那栋老房子里,究竟还发生过哪些秘密?一定会有的吧,就算不是在我家,隔壁邻居的楼上楼下,总有些不为人知的往事。
今晚,这个秘密就在眼前,就像一只被加热的瓶子,再调大些火侯,就会彻底爆裂。
小东阿姨,青青阿姨,还有我妈妈。
她们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在说谎。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她们三个,全都说谎了。
但,我又不可能指望她们自己说出来。
忽然,我清了清嗓子,第一次高声说,我去档案局调1977年你们的高考考卷,好吗?
沉默。
比打在屋顶上的暴风雨更沉默,沉默得震耳欲聋。
子夜,零点。
不知是谁要脱口而出之际,身后的精神病院却响起刺耳的声音……警报声!
听得撕心裂肺的!我忍不住打开窗户,风雨小了些,荒野里亮起几盏光,从精神病院方向,变成几个人影,推开这间餐馆的门。
几个不速之客,分别穿着白色外套,两个强壮的男护工,还有个似是医生模样,却并非刚才那个男人。
对不起,你们是什么人?这些家伙就像审问似的,仿佛我们是逃跑的病人。
我们是今天来探望病人的。
哦,我记得,医生眼里布满血丝说。
前面的公路被水淹了,我们在这里躲雨,我这样跟他解释。
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说话同时,两个护工在小餐馆里搜查,包括厨房和厕所也没放过。
是有精神病人脱逃了吗?
说话的是小东阿姨,看到对方点头,她已猜到几分,回头说,是他吗?
你们看到他了?
是不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医生说着拿出一张精神病院的表格,写着病人的名字,还有张大头照,赫然就是几小时前,出现在这里的神秘男人。
他是病人?
青青阿姨快要晕过去了,妈妈扶了她一把,我保持镇定道,他说是精神病院的医生。
嗯,这就是他最显著的症状,妄想自己是资深的精神学科医生,这样就能解释他为何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了。
说话的才是真正的医生,为了让我们确信他也不是精神病人,他掏出医生的证件给我们看了一圈。
你们才发现?
晚上点名时发现人不见了,调出录像监控显示,下午他就逃出去了。
嗯,我们是见到他了,在这吃了碗葱油面,还跟我们聊了一会儿,将近十点钟离开的。
册那,这疯子够胆大的,明明逃出了精神病院,还在门口坐了那么久!一个护工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现在雨小了,路应该通了,你们有车就快回去吧,留在这里很危险,两年前,有个性变态的病人逃跑,躲在附近一间农舍,杀了别人全家。虽然,今晚逃走的病人没有暴力倾向,但还是要小心点。
其实,知道那个王八蛋是精神病,就算外面下冰雹,也得快点回去了。
我重新发动车子,妈妈坐在我身边,小东阿姨和青青阿姨在后排。
午夜,雨刷刮开档风玻璃上的雨点,瀑布般流淌下来,大光灯前的郊外小道,不知哪里潜伏着精神病人。今晚,犹如蒲松龄的世界,妖异而模糊。
谁都没说话,但我能感到她们的出气声,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仿佛各自庆幸——精神病人的鬼话,谁信啊!
小心地开过不到十分钟,道路上的积水果然退了,车速加快。
忽然,灯光中窜过黑影,几乎紧贴地面飞过。
靠,我无法躲闪,急刹车也来不及,若是猛打方向盘,很可能冲进路边水沟,只能闭上眼睛碾压过去。
再停车。
刚才微微一颠,车轮下碾过了什么?其他人也感受到了,小东阿姨回头看着,青青阿姨却催促我快点往前开。
手心里都是汗珠,窗外的雨越来越小,车里却仿佛暴雨一场。
但我犹豫片刻,还是选择踩下了油门。
不知道压着了什么。
命运吧,我想。
继续往前开去,很快摆脱了乡间公路,上了回市区的高速。车里的三个女人,依然寂静一片。虽然她们都很疲倦,但我想一个都不会睡着。我重新打开电台,深夜的古典音乐频率,响起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
那一晚,送我妈和她的闺密们的回家路上,不知为何,我的脑中,却浮现起那个穿着海魂衫的男子。他叫志南,死的时候,应当比我年轻,死在车轮底下,死在一座孤岛上。
一个月后。
我托了许多层关系,包括档案局的领导,依旧无法调出1977年的高考试卷——除非我是某大大。
但我查出了抗美的高考成绩单。
结果却让人惊诧,她的总分不高,远远低于最低分数线,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中有一门课考了零分——语文。
语文零分?
这怎么可能?若说数学零分,倒也情由可缘,语文从来没有零分的,就算作文打了零分,其他也不可能错光,除非交白卷。
但我没有看错。
档案馆的灯光下,明亮却不刺眼。我看着这份成绩单,眼前成排的台子宛如课桌,紧闭的大门有管理员守着,宛如三十多年前的监考老师。而我就是小东,或者青青,或者抗美,坐在决定命运的椅子上,看着想象中的试卷……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萃取到白兰花的香味,外公外婆的小阁楼里的气味啊。
离开档案馆,我直接开车去了精神病院,独自一人。
回到那栋灰暗的建筑前。门口的小餐馆已经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送盒饭的快递员,大概还是有医生和护士不满意伙食。
但我没有看到抗美阿姨。医生说一个月前,我们去探望过抗美以后,她的情绪就极不稳定,现在必须隔离,什么人都不能见。
那个医生,就是子夜时分,带着护工出来追捕逃跑的精神病人的那位。
他说,那个把自己想象成精神病医生的病人,到现在也没有被抓到。因为没有过暴力犯罪的前科,公安局没有下达通缉令或协查通告之类的。好在那个人没什么家属,从小就是父母双亡的,否则要被烦死了。不过,院长还是为此写了好几页检查。
逃跑的精神病人,跟抗美阿姨的关系好吗?
他们几乎是唯一的朋友……事实上,抗美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经常管他叫学文。
学文早就死了十多年了。
我知道。
医生,这么说来,抗美把自己的一辈子,全都倾诉给了那个病友。而那个人,就在抗美的面前伪装成医生?
嗯,他最喜欢给人做逻辑分析,除了假装给人看病,还经常给人分析各种疑问,许多秘密真的被他说准了——说实话,如果没有精神病的话,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警官,或是推理小说家。
说到这里,我才发现医生的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日本与欧美的推理小说。
我问不到更多的答案了,也不想再去打扰抗美阿姨,更没告诉妈妈在内的任何人,关于我的第二次精神病院之行。
返回市区的路上,我格外小心开车,以免再轧到什么奇怪的东西。车载音响里是肖斯塔科维奇的C小调第8号交响曲,缓慢碾轧过荒野泥泞的道路,也许还包括某些尸体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