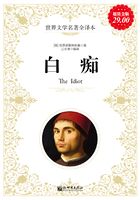
第12章 与女士相处(3)
“您干吗老生气,真不明白,”将军夫人早就在不停地观察这两人说话时的脸色,这时接口道,“你们究竟在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什么小指头?真是废话连篇!公爵说得很好嘛,不过有点伤感。您干吗把他弄得灰溜溜的?他开始的时候还笑,可现在全蔫了。”
“没什么,Maman。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要不,我倒想问您一件事。”
“我见过死刑。”公爵答道。
“您见过?”阿格拉娅叫道,“我早就该猜到这点了嘛!这就齐了。您既然见过,怎么能说您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嗯,我这话说得不对吗?”
“难道在您住的那村子里也杀人?”阿杰莱达问。
“我在里昂见过,我跟施涅台尔上里昂去,他带我去的。刚到就赶上了。”
“怎么样,您看得津津有味吗?大开眼界?大有教益?”阿格拉娅问。
“我根本没有看得津津有味,这事以后,我还闹了场小病,但是不瞒你们说,当时我都看呆了,不想看也不行。”
“换了我,也会紧盯着看的。”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连报上都登过这些女人的事。”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么说,他们想以此来说明是男人的事喽。这种逻辑真了不起。您自然也是这么认为的喽?”
“您就讲讲死刑吧。”阿杰莱达打断道。
“我很不愿意现在……”公爵慌乱地说,好像还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说给我们听似的。”阿格拉娅挖苦道。
“不是的,这是因为刚才我已经给人家说过一遍关于这次死刑的事了。”
“给谁说的?”
“给府上的听差,当时我正在等候……”
“什么听差?”从四面八方传来疑问。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位,头发花白,红红的脸;当时我坐在前厅里恭候谒见伊凡·费道洛维奇。”
“这倒是新鲜事儿。”将军夫人道。
“公爵是民主派嘛,”阿格拉娅抢着说道,“嗯,既然能说给阿列克谢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们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再次请求。
“刚才倒的确,”公爵对她说道,又有点兴奋起来,“您问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倒的确有个想法,想提供您一个题材:就画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前一分钟的脸,那时他站在断头台上,还没横倒在刀下的木板上。”
“怎么画脸?就画他的脸?”阿杰莱达问,“这题材多怪,这算什么画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呢?”公爵热烈坚持道,“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这样一幅画。我想给你们讲讲……不过,以后有机会再说吧……这幅画使我受到极大震动。”
“关于巴塞尔的那幅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您就先给我说说这幅行刑图吧。您能把您想象中的情形告诉我吗?这脸怎么画法?就只画脸?这脸究竟是怎样的呢?”
“就在临死前那一分钟,”公爵谈兴正浓,沉湎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显然霎时忘记了其余的一切,开始说道,“就在他登上扶梯,刚刚跨上断头台的那一刹那。这时,他向我这边看了一眼,我望了望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但是,这事该怎么说给你们听呢!我非常非常想,由您或者随便哪位能把这情景画下来!最好是您!我那时候就想,这画肯定是有益的。您知道,要画好这幅画必须先把一切好好想象一下,把这以前的一切一切都好好想象一下。他住在监狱里等候行刑,心想,刑期起码还有一星期,不知为什么他寄希望于通常的审批程序,判决书还要送到某处审批,一星期后才能批下来。可是这一回却因为某种情况,突然简化了手续。”
“清晨五点,他还在睡觉。这发生在十月底,五点钟,天还很冷,很黑。监狱警官走进来,带着狱警,轻微地推了推他的肩膀,他用胳膊肘支起身子……看见了灯光:怎么回事?九点后处决。他起初因为睡眼蒙眬不相信,还争辩说,公文得过一星期才能批下来,可是当他彻底醒过来以后,也就不再争辩了,闭上了嘴……人家是这么告诉我的……后来又说了一句:这么突如其来,真让人受不了……说完又闭上了嘴,他已经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这时又花了三四个小时来做众所周知的事情:神父呀,用早餐呀。早餐时,还给了他葡萄酒、咖啡和牛肉,然后梳洗打扮,最后押上囚车去游街,上断头台……我想,他游街的时候一定以为,他还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可以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大概在想:时间还长着呢,还剩三条街好活呢,瞧,走完这条街后,还有一条街,之后,还有路北有家面包店的那条街……到面包店,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周围人山人海,人声鼎沸,一万张脸,一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必须经受住,主要是他必须忍受这样的一个想法:这儿有一万人,可是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要被杀头,要被杀头的只有我!嗯,这一切还只是开场。有一张小梯子通上断头台,可是他在这小梯子前突然哭了,而这是个彪形大汉,据说是个作恶多端的恶棍。一路上,神父不离左右,跟他一起坐在马拉的囚车上,一直跟他说话……其实,他未必听得见:即使听,听了两句也就不知所云了。一定是这样!
“最后,他开始登上那张小梯子;他的两腿捆绑着,所以只能迈着小步向上攀登。看来,神父是个聪明人,他不再说话了,而是一个劲地让他亲吻十字架。还在梯子下半部的时候,他的脸色就十分苍白,等他爬到顶上,站到断头台上,脸刷的就白了,白得像纸,完全像张白色的书写纸。他大概两腿发软、发麻,想呕吐……仿佛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感到痒痒……从前,当您感到惊慌,或者处在一种非常可怕的时刻,您虽然神志清醒,但却丝毫无力支配自己理智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比如说,必死无疑,房子要塌了,向您身上压过来了,您会猛地横下一条心,索性坐下去,闭上眼睛,等着……听天由命,豁出去了!就在这时候,即发生这种瘫软无力状态的时候,神父赶紧快速地忽然把十字架默默地送到他的唇边,这是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银的,四边形的……一刻不停地频频送过去。十字架一碰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有几秒钟似乎活了过来,两腿也能走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急急忙忙地连连亲吻,仿佛他急于不要忘记抓住什么东西似的,留着,万一有用呢,但是此刻,他未必有什么宗教意识。就这样直到横躺在木板上……奇怪的是,在临刑前的最后几秒钟,很少有人昏过去,相反,这时脑子特别灵活,大概活动得也最厉害,就像一架开动的机器似的,我想,这时肯定有各种想法纷至沓来,但是这些想法都是有头无尾,或许还是很可笑的、没头没脑的。瞧那人东张西望……脑门上有个疣子,瞧这刽子手,底下的一枚纽扣都生锈了……
“与此同时,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怎么也忘不掉的视点,他绝不会昏厥,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活动和旋转。试想,就这么一直到最后四分之一秒钟,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横放在断头墩上,在等候,而且……他知道,会猛地听到头上的铁索哧溜一声向下滑落的声音!这一定听得见!如果我躺在那里受刑,我一定会特意去听,而且一定听得见!这时,也许只有十分之一秒的一刹那,但是一定听得见!你们不妨想象一下,至今还有人在争论,也许,当脑袋飞落的时候,大约有一秒钟的时间,他也许会知道脑袋飞落了……这是什么观点啊!如果有五秒钟,那又怎样呢!……您可以画一座断头台,画得能看清梯子的最后一级,作为近景,就看得清这最后一级,犯人已经踏上这级梯子:脑袋,像纸一样苍白的脸,神父把十字架送过去,他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看着,心里全明白。十字架和脑袋……这是画的中心,神父。刽子手,刽子手的两名助手的脸,还有向上仰望的几颗脑袋和几双眼睛,这一切都可以画作远景,画模糊点,作为点缀,就画这么一幅画。”
公爵说罢,望了望大家。
“这当然不同于寂静主义。”亚历山德拉自语道。
“好吧,现在就说说您是怎么恋爱的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诧异地望了望她。
“我说,”阿杰莱达似乎急匆匆地说道,“您还欠我们一段关于巴塞尔那幅画的故事,但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么恋爱的,您不必抵赖,您一定恋爱过。再说,您现在一开始谈这种事,就不会坐而论道了。”
“您一讲完就立刻对您所讲的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突然指出,“这是干吗呀?”
“真是的,这话问得多蠢。”将军夫人愤怒地望着阿格拉娅,生硬地说道。
“不聪明。”亚历山德拉附和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话,”将军夫人对公爵说道,“她是存心气您,其实,她有教养,完全不是这么蠢,她们向您这么乱提问题,请您别介意。她们大概想干什么淘气的事儿,但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看她们的脸就知道。”
“我看他们的脸也知道。”公爵说,对自己的话特别加重了语气。
“这话怎讲?”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对于我们的脸,您知道什么呢?”其他两姐妹也感兴趣起来。
但是公爵沉默不语,神情很严肃,大家在等他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低声而又严肃地说道。
“您是存心想引起我们的兴趣,”阿格拉娅叫起来,“瞧您那副得意样!”
“嗯,好吧,”阿杰莱达又急忙说,“既然您是一位通晓脸的行家,您一定恋爱过。可见,我还猜对了,您就快说吧。”
“我没恋爱过,”公爵仍旧低声而又严肃地答道,“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那是怎样的幸福法呢?”
“好,我来讲给你们听。”公爵仿佛在深深的沉思中说道。